达伯霍瓦拉|从《瓦格号》到《花月杀手》
- 综合
- 2024-11-14 11:54:26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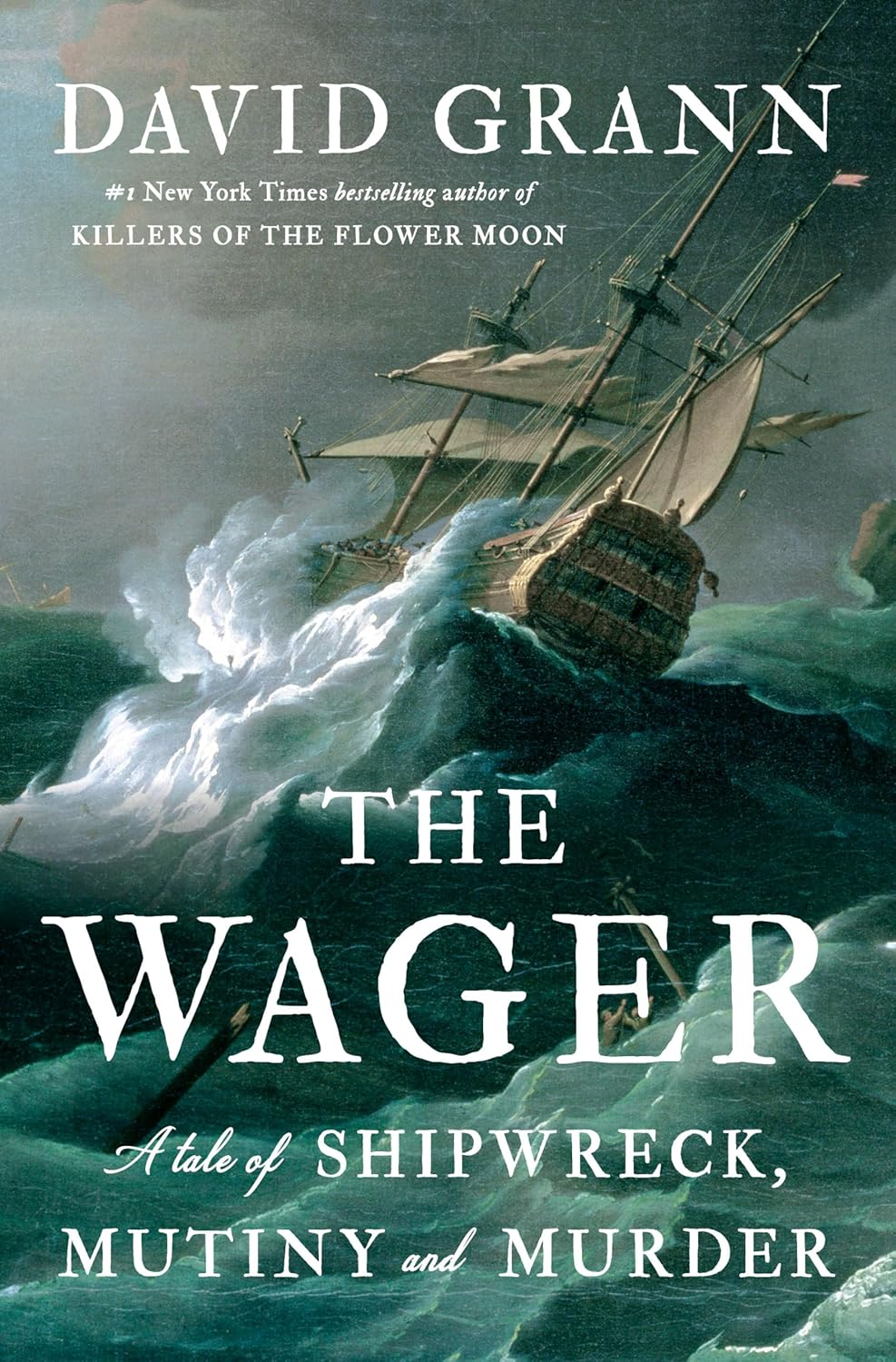
The Wager: A Tale of Shipwreck, Mutiny and Murder, by David Grann
当英国与西班牙在1739年爆发战争后,英国政府派出两支舰队进攻敌方在南美洲的属地。新晋升的海军中将爱德华·弗农(Vice Admiral Edward Vernon)率领一支由近两百艘船只和近三万人组成的庞大舰队开往西印度群岛,他此后会因为成功占领巴拿马的波特韦洛(Porto Bello)而声名大噪,他们还会试图夺取西班牙在该地区的其他重要属地。在这项主要任务外,乔治·安森准将(Commodore George Anson)也率领一支由六艘战舰和两艘补给船组成的舰队出征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将绕过合恩角去袭击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港口,最终会捕获一艘著名的西班牙珍宝帆船,这条满载白银的帆船当时正从墨西哥驶往菲律宾。对安森舰队来说,从一开始几乎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都出了错。由于船只舾装的工作一拖再拖,安森舰队直到1740年9月才出发。主要问题之一是水手短缺。海军当时对人手的需求如此迫切,除了强行征召甚至绑架数百名商船海员(其中许多人没多久就逃离战场)外,他们还从切尔西医院拉来了五百名年老体弱的退伍老兵。这些人中有近一半都没能走到朴茨茅斯;而那些走到朴茨茅斯的人里面还有一些不得不用担架抬上船。
上了船的这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弗农的远征军是当时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击部队,但他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就惨遭大败。当时他们试图攻占卡塔赫纳(Cartagena),围城数周之后就有大约一万名士兵丧生,其中大部分死于黄热病、疟疾和痢疾。还有几乎同样数量的人在战斗中受伤。弗农不得不撤退,美洲沿海的战况就此陷入僵局,其重要性被欧洲的事态发展赶超。最终,1744年6月,安森舰队中的“百夫长”号踉踉跄跄地驶回了朴茨茅斯。他成功地俘虏了一艘西班牙珍宝帆船,并勇敢地完成了环球航行,但其代价也令人震惊。其舰队中其他所有船只都因伤寒和坏血病而严重减员,要么被迫返航,要么就在途中失事。近两千名参加远征的将士中,回到国内的人数是一百八十八人。
安森舰队中最小的那艘船名为“瓦格号”,它原本是一艘平底商船,被海军改装成武装货船,并以时任首席海军大臣、此项秘密任务的策划者查尔斯·瓦格的名字来命名。在数十名船员因病丧生后,瓦格号于1741年5月在智利沿岸的可怕海域搁浅沉没。船上原有大约二百五十名水手和士兵,其中一百四十五人于沉船事故中幸存,逃到了一个荒凉的无人岛。他们后来几乎全部丧生,大多数死于饥饿。但有极少数人经历重重险境之后,于1742年3月到1746年7月间分批回到了英国,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单凭一艘简陋帆船成功穿越麦哲伦海峡的壮举。幸存者中包括船长戴维·切普(David Cheap)、他的副手罗伯特·贝恩斯(Robert Baynes)、首席炮手约翰·布尔克利(John Bulkeley)、木匠约翰·卡明斯(John Cummins)以及三名年轻的海军军官约翰·拜伦(John Byron)、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和艾萨克·莫里斯(Isaac Morris)。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路线返回祖国,而对海难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也相互矛盾——都指责对方造反、谋杀和背叛。
航海探险、海难和求生的故事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读者中颇为流行。海军军官应该记录准确的每日航海日志和报告,那些描述著名探险事迹的畅销书也往往大量采用这些第一手材料。在瓦格号船员随身携带的书籍中,有一本讲述海军上将约翰·纳尔伯勒(Admiral John Narborough)于1669年至1671年间远征巴塔哥尼亚的书,他们在此后的苦难历程中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这本书。他们也应该知道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的故事,这位海军军官在智利海岸的一个小岛上过了四年多的孤岛生活,直到1709年才获救——丹尼尔·笛福1719年出版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部分内容就是源自他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瓦格号上有一名水手名叫威廉·鲁滨逊·克鲁索——如果他没有在启航前就做了逃兵,那么在那些被迫流落南洋孤岛的人中可能就会包括了一位真实的鲁滨逊·克鲁索。
瓦格号的幸存者中后来有不少出版了关于他们经历的详细记录——目的是谋利,或者为了证明他们犯下的争议行为是正当的,也为了回应公众对他们故事的巨大兴趣。还有一些则私下为海军部的老爷们写下了他们的故事。船长切普枪杀了一名手无寸铁的水手。还有其他人也被谋害。船长被手下的海兵队员关押,然后被大多数船员遗弃在岛上。也有其他人在途中被杀或被遗弃。还发生过一些食人事件。其中许多行为根据海军法规都应受惩罚甚至是死罪。切普船长回国后,所有幸存者都被传唤到停泊在南部海岸的一艘军舰上接受军事审判。虽然这场审判最终并未将任何人送上绞刑架,但却产生了更多流传至今的记录。
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自从问世伊始就一直被传述至今。基于其丰富的档案资料,现代也颇有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戴维·格兰对此的叙述是你能读到的最好版本——其叙事既有史诗般宏大气势,又节奏明快,令读者宛如置身事内,经历一系列复杂而对错难分的事件,使人感觉不仅能够了解这些人的遭遇,还能了解到这一事件能够在何等程度上融入十八世纪英国的帝国主义冒险那段漫长而痛苦的故事。
格兰是如何做出这番成绩的呢?他的秘诀有三个要素。首先是研究。他多年来阅读了所有曾被印刷出版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并从档案中挖出了原始手稿。他与当代在此领域专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向他们请教十八世纪战舰是如何建造,船员们在船上和陆地上的生活又是怎样的。他甚至亲身前往瓦格号沉没的地点——后来被命名为瓦格岛——目睹了故事中难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第二是结构。每一短章都以某个单一事件或主人公为中心,通常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作者在此巧妙地引用和转述同时期的资料。它总是以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或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开始,并往往以一个悬念结束。此外,每一章节本身又再由多个更短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只包含几段文字。这种场景之间的不断切换,几乎给人一种电影般的体验。格兰的写作技巧作为最后一味元素,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能够掌控叙事的节奏,就像在一部电影中那样。有的时候只用一两句话,我们就历经了悠长岁月;但有时事情的发展也会非常缓慢,我们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凶猛的风暴,或者一场致命传染病疫情之中,或者目睹一群被遗弃,注定将面对死亡的海兵队员的最后时刻——他们看着战友扬帆远航,但还勇敢地高呼“天佑吾王!”马丁·斯科塞斯已经开始着手将《瓦格号》改编成电影,这并不令人惊讶:它读起来已经像是电影了(《花月杀手》即改编自格兰之前的作品)。
这本书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也依赖于创作者的一些自由发挥,其叙事结构要求对时间顺序不断的细微调整。例如,原始资料明确指出,船员们在荒岛登岸后就几乎立即组织起来,从沉船残骸上尽可能多地捞取食物和其他补给品。不久,一些住在独木舟上、往来于邻近海岸线周边的卡瓦斯卡尔部落原住民造访当地,为船员们提供了肉食和鱼类。但在格兰的书中,这些事件都被分开处理,因为每一章都必须有一个单独的重点,将其逐一串联起来会增强它们各自的影响力。因此,一开始有几章讲述的是那些流落荒岛的人们拼命寻找食物,情绪跌入谷底。之后,才是他们从沉船中找到补给,并逐渐适应集体生活的章节。最后,作为一个惊喜,卡瓦斯卡尔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得知了他们在这片地区的历史,以及他们与切普船长及其船员的互动。
格兰也让基于原始资料的推论更加有血有肉。有一份资料提到,在荒岛登陆后的第一个早晨,饥饿的人们设法“杀死了一只海鸥,摘到了一些野山药——人们立刻把(这些收获加上一些面粉)放入锅中,再加入大量的水煮成汤,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在格兰的笔下,这是一个生动的场景,充满了完全可信却又全然虚构的细节:
最后,有人打中了一只海鸥,切普船长命令把它分给大家。
大家把树枝架在一起,从火药盒里拿出打火石和金属片,费力地点燃那些潮湿的木头。最后,火焰终于噼里啪啦地冒了出来,烟雾在风中萦绕。老厨子托马斯·麦克里把海鸥拔了毛后放进一个大锅里煮,再撒上一些面粉,煮成一锅浓汤。热气腾腾的汤就像神圣的祭品一样,被舀进他们捞上岸的几个木碗里。
此类合理演绎不断演变成全然的杜撰。饥肠辘辘的约翰·拜伦在岸边淹死的船员尸体中拾荒,偶然发现了被冲上岸的一桶咸牛肉。约翰·布尔克利看到拜伦“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便把他迎进自己刚刚搭建的一个舒适的避难所,让他在火炉旁取暖。在幸存者返回故土的漫长航程中,有一队人游泳上岸寻找补给,其中一员海兵詹姆斯·格林汉姆(James Greenham)“渐渐疲惫,难以支撑。莫里斯试图去救他,但那个海兵还是淹死了”。所有这些场景都如同电影一般,而且也都是为了戏剧效果,部分甚至全部虚构出来的。这些微小的虚构有助于让人物鲜活起来,暗示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产生共鸣——对任何创作历史故事的作家来说,这都是艰巨的挑战。
格兰的宏大主题其中之一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历史本身都是一种编造。不同人的故事相互冲突;不同人的视角各不相同;不同人为了迎合自己而捏造事实。有权有势者的叙事总是更有可能压倒下层人民的故事。对于瓦格号的幸存者来说是这样,对于历史总体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历史往往会让无权无势者和战败者噤声。《花月杀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俄克拉荷马州的奥萨奇印第安人与其他土著民族一样,也被殖民者强行剥夺了祖先的家园,被迫迁往他处。到了1920年代,在他们的新家园土地之下发现了石油,部落中仅存的两千余名成员因此致富。但不久之后,他们开始逐一离奇死亡——被枪杀、被毒死、被燃烧弹烧死在床上。总共可能有一百多名男女和幼童被杀害,但当局对此漠不关心,甚至没有留下记录。一心牟利的白人商人精心策划了这场大规模屠杀,而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遭遇到的暴力侵害漠不关心和同流合污则成为了掩饰这一罪行的更为普遍的文化背景。二十世纪美国立法机构及印第安人事务局所秉持的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政策更助长了这一行径,在部落富裕起来后,他们就对部落实行一种腐败的“监护”制度;奥萨奇部落民可能被认定为“无能”,从而让他们的资产被外人所控制。
在《瓦格号》一书中,欧洲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所有暴行背后的暗流。尽管格兰提到了英国海军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提供保护,但书中的英雄人物却显得与其没有半点关系。书中并没有提到,安森准将在战前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英属北美奴隶制的首府——驻扎了十年,他在那里是当地精英阶层中颇受欢迎的一员,也在当地大肆投资地产。书中也读不到在此次的秘密任务启动之前,安森和他的“百夫长号”曾经有整整两年时间为驶离西非海岸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贩奴船护航(塞尔柯克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正是在执行这样的任务)。
“瓦格号”这一船名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得以流传下来,并且继续与跨大西洋奴隶制政治密切相关。英国皇家海军在1744年下水了一艘二十四门炮的同名新战舰来取代失事的那艘船。这艘重生的“瓦格号”两年后开始在牙买加协助维持治安,对象是被奴役的人群,力图保护这种绑架非洲人的贸易。船长阿瑟·福雷斯特(Arthur Forrest)曾参与过针对波特韦洛和卡塔赫纳的军事行动,此人来自当地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在他为自家土地买来的奴隶中,有一位来自西非的军事领袖名叫阿庞戈(Apongo)。福雷斯特将此人改名为“瓦格”,与他的新船同名,并让“瓦格”与其他非洲人一起在那条船上当了一年多的水手。然后,他被送去福雷斯特在牙买加最西部拥有的蔗糖种植园劳作。1760年,这位“瓦格”领导了当时在大英帝国发生过的最大规模奴隶起义——如今被称为“塔基起义”(Tacky’s Revolt)。
与这些具备更为广泛视野的背景资料相比,格兰一书中对瓦格号上唯一留下记录的有色人种水手(当时船上很可能有更多的有色人种:那个时代的海军成员混杂多样的程度早已闻名)的处理,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局限性。此人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伦敦人,名叫约翰·达克(John Duck)。格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达克“面临着白人海员所没有的威胁:如果在海外被俘,他可能会被当作奴隶出卖”。在书的结尾,他如愿以偿地面对了这一命运。
莫里斯和他,还有另外两个人一起跋涉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外。但在那里……他遭受了每个自由黑人水手都害怕的遭遇:他被绑架并卖作奴隶。莫里斯不知道他的朋友被带去了哪里,是矿山还是田野——达克的命运就此不得而知,就像许多人的故事永远无法被讲述一样。
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似乎能够为格兰关于历史中的不公平和沉默的论证画上一个恰当的结尾。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读到,达克、莫里斯还有他们的两个同伴塞缪尔·库珀和约翰·安德鲁斯曾被友好的巴塔哥尼亚原住民所救,原住民在接下来两年半的时间里“带着他们从一个村庄前往另一个村庄,在每个地方都会停留数月”,直到他们到达西班牙领地。直到这时,事情才出了差错:达克被当成了奴隶,另外三人则被无情的西班牙人关押起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格兰凝练而整齐的叙事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把他试图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达克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当了多年的奴隶,他们被买卖,被强迫劳动——并非被西班牙人,而是被特胡尔切(Tehuelche)部落的人如此对待。特胡尔切人对待俘虏的习惯向来如此,在这个部落之中还有许多从殖民地边境地区劫掠而来的西班牙妇女。英国水手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说服抓住他们的人,使其相信西班牙人会为他们支付丰厚的赎金,然后那些英国人才穿越了印第安人领地,被送往千里之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换取金钱。他们作为奴隶的遭遇与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及其后裔施加的奴役截然不同。美洲原住民的奴隶制与非洲本土的奴隶制类似,主要是一种家庭内部的非自愿奴役。它并不意味着像在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那样,在大种植园或银矿里被活活累死,或者经常受到可怕的虐待。莫里斯在他的叙述中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打柴取水,给他们杀死的每一匹马剥皮;虽然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但我们受到了十分人道的对待,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虐待我们。”
约翰·达克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的同伴们小心翼翼地指出,用他们的话说,他是一个“穆拉托”(mulatto,黑白混血儿),换句话说,他的父亲或母亲是白人。也许他是约翰·达克船长的儿子,这位船长是安·达克的家长,1709年前后活跃于伦敦及周边。莫里斯和其他人后来声称,巴塔哥尼亚人拒绝让达克也被赎回,因为他“与那些印第安人的肤色太接近”,“坚持认为他是印第安人,所以他们才把他留下”。这点除了让我们对达克的肤色有所了解之外,还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很难猜测特胡尔切人的动机,但这一点同样令人好奇——尤其是另外三名英国水手为特胡尔切人换来了丰厚的报酬。如果达克是白人,在他与莫里斯、库珀还有安德鲁斯一同经历了这段历程之后,他们会把达克留下吗?此三人是不是为了赢得自己的自由而出卖了达克?这已经不得而知。
甚至有可能,他的伙伴们后来在英国对达克的命运的描述,是在为他作掩护。在西班牙领地为其他水手支付赎金的人是当地阿西安托(Asiento,持牌黑奴商人)的英国代理人。这些水手此后又再被囚禁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们“受到的待遇更像是奴隶,而非战俘”。也许达克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冒险;可以想象,对他来说,作为一个黑皮肤的人,进入敌对的殖民地的风险要大于作为巴塔哥尼亚人奴隶的不适。他的同伴们在重获自由后不久曾经简短地透露,在被特胡尔切人奴役的几年里,他们每个人都“娶了一个拉丁裔女人为妻,有些人还留下了孩子”。也许,远离家乡的达克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是没有留下记录的和被奴役的人,无论他们经历了何等极端的困境,他们都是自己故事中的演员。也许他是自己选择了留下。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伦敦书评》,获作者授权翻译)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