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大会︱陈光宇:东西方古典文明萌芽时期的文字
- 生活
- 2024-11-08 12:30:04
- 9
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参会中外专家60余人,陈光宇教授做主旨报告《东西方古典文明萌芽时期的文字》。
陈光宇教授为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杰出荣休化学教授暨罗格斯大学东亚学系兼任教授(1998年至今),现主要从事上古中国(Early China)领域研究,主要方向涉及甲骨文与商代文明研究、汉字起源与其他起源文字比较研究、汉字生态学理论构建、先秦朱砂与水银工业、古文字海外教学(甲骨文、金文、简帛)等。陈光宇教授既是杰出的化学家,也是知名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学者,享誉海内外。
东西方古典文明萌芽时期的文字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参加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能有机会在美丽的雁栖湖旁与来自四面八方世界各国许多领域的学者专家相互交流。众所周知,古典学的空间源头在东方是先秦中国,在西方是古希腊。而古典学的时间源头就牵涉到东西两大文明的探源问题。
文明探源首要要工作就是文字溯源, 研究文字起源的时间范围、聚落地点、以及发明产生文字的条件,包括生态环境、地貌景观、生产力,商业行为等等。特别是文字发明的关键动力。人类历史上独立发明形成文字系统的文字称为自源文字或起源文字,目前所知,至少有四种:两河流域的苏美楔形文,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体文,中美洲的奥梅克-马雅文以及黄河流域的汉字甲骨文。产生这四种自源文字的地域均在北纬30度左右,显示文字发明与人类所处自然环境有一定关联。目前汉字最早的考古证据是安阳出土十数万片的商代甲骨。甲骨文的时间与苏美文、埃及文的时间相距将近1500年。但是甲骨文是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汉字起源时间毫无疑问应该远在商代 (1600-1046 BCE)之前,汉字溯源需要在新石器时期与商代之间探寻。
新石器时代将近一万处的文化遗址遍布中华大地,多有刻符出土,知名的如贾湖、双墩、大汶口、良渚、仰韶、龙山等遗址是文字考古探源的首选之地。同时汉字探源的视角也应该扩及到其他自源文字,除了可以收攻错之益外,自源文字的对话比较也有助厘清人类文明文字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
文字是含有特定音素,特定意涵与特定形体的符号。这个定义可以精确的表达为:G(文字) = G:{+P,+S}。 其中G 代表形,P代表音(phoneme), S代表义(sense)。东汉许慎形容文字发明的过程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新石器时代晚期,种种文化元素的累积酝酿,开始有需要将特定符号与特定的语音结合起来,于是产生由“符” 至“文” 的质变,有“依类象形”的“文” 出现,这是文字发明的第一阶段,“文”可以记录人名或地名,但还不足以记录口语。“文“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初文”或“原始文字”。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酝酿,部分的“文” 被用作专门表音的符号,于是产生由“文”至“字” 的第二阶段文字发明,经过两个阶段的文字发明,文字才能发展为成熟系统,可以表示语气、语法、记录语言。就器物刻符而言,在“文”的第一阶段,多以单符或双符出现,而经过第二阶段的“文字”才可能以成行或成列的串符出现。
目前国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刻符是否文字 还缺乏共识,主要原因是:(1)缺乏客观精确的文字定义,往往将图符、记号与文字混为一谈。(2)忽视人种、语言信息。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景观差异明显,文化面貌多样。大汶口、良渚等文化的人种与语言系统可能与陶寺、二里头不同。在缺乏古基因检测数据情况下,将大汶口或良渚刻符与汉语系统的甲骨文、金文只作形体比较,意义不大。(3)忽视刻符在考古发掘的出土信息,因此无法利用考古情境来推测刻符可能的意涵与功能,从而分析刻符是否代表文字。
考察两河流域乌鲁克(Uruk) 遗址出土的泥版刻符,从考古情境与泥版刻符的叙事情境,学者分析在许多泥版出现的两个刻符代表人名,符合形音义的基本文字条件,从而论证苏美尔人至少在公元前约3100 年左右已经发明文字。同样,考察埃及涅卡塔尔(Naqada)遗址出土的纳玛石板与石制令牌头上的精细刻图,可以确定其上有特定刻符代表法老王名,从而论证埃及人至少在在公元前约3100年左右已经发明文字。而新世界的中美洲奥梅克-玛雅文明先以拉汶塔(La Venta)遗址附近出土的滚筒陶玺刻符有王名来论证玛雅文字定点在公元前650年。其后玛雅文学者对于喀斯卡石块刻符的研究分析,从石块实体,刻符排列,以及刻符形体在玛雅文化具有特定文化意涵来论证它们代表文字,从而将中美洲文字发明时间上推到公元前900年。
参考比较境外自源文字的溯源研究,特别是如何结合考古情境分析与文字定义来论证器物刻符是否文字的文字考古例子。在境内庞大的新石器时代刻符材料之中,我们首先选择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尊刻符,以及山东龙山时期的丁公村陶片刻符来考察这些刻符是否文字。
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集中出现在陵阳河与其相邻的大朱家村及杭头等三个遗址。陵阳河遗址在莒南县陵阳乡大寺村附近陵阳河南岸,发掘的45座墓葬中有25座集中在陵阳河南侧,称为河滩一组墓葬墓坑大致为西北向,排列有序,明显经过规划。墓葬均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可以再分为三个时段:早(3000-2800 BCE)、中(2800-2700 BCE)、晚(2700-2500 BCE)。其中陵阳河遗址有4件出土于墓葬,分别为M19、M25两座中段墓及M7、M17两座晚段墓。M19及M25的出土资料完全, M19墓主手持石钺,腰挂陶制牛角形号角; M25墓主戴有石环、石管,显然均为部族首领或贵族。二墓均有大口尊竖立于墓主脚端,大口尊各有一刻符,分别是菱形刻符与封字形刻符,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例外,刻符均面向墓主。考虑刻符可能的作用,及刻符面向墓主的情境分析,刻符最有可能代表墓主的名字。语音呼唤人名,瞬间即逝。文字记录人名,永远长存。陵阳河刻符面向墓主,仿佛永远呼唤墓主,象征墓主永远存在。远古苏美文化视名字为实体,没有名字就没有实体存在。远古埃及,人名刻于墓壁,以资他人呼唤,是虽死犹生的保证。结合苏美、埃及对名字的敬畏崇拜,陵阳河刻符代表墓主人名是最为合理的选项。陵阳河刻符如果确为人名,表示具备了形、音、义三个文字基本元素,一如埃及的王名、苏美的人名,应该视为文字,我们可以推定山东沂沭地区在公元前2800年已经有文字存在,可以称之为大汶口文字。它们是否汉字的直接祖先,有待未来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人种基因鉴定。
丁公陶片长4.6-7.7,宽3-3.2cm, 厚0.35厘米,面积约25方厘米, 来自直壁平底盆的底部, 平底盆的材料为泥质磨光灰陶,是典型的龙山文化陶器。现存5列11符。刻符笔划有致,刻画熟练,圆转流畅,确有章法顺序。多为连笔,也有圈笔、曲笔、弧笔、直笔,与目前所见古彝文极为相似,二者显然使用相同的笔画系统。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些丁公刻符的形体与古彝文竟然高度相似。丁公村陶片出土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遗址,距莒县不过百里。陵阳河大墓与丁公遗址址,时间相距700年。龙山文化晚期的个别古国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与客观条件来进行完成第二阶段的文字发明,产生成熟文字系统。丁公陶文出土于龙山城址的东墙发掘的灰坑H1235。该灰坑出土的全部文物均属龙山文化晚期的偏早时段(2200-2100 BCE)。丁公陶文的连笔、曲笔刻划可用龙山时代的骨针、骨锥、骨筓、在陶坯上复制,但难以在烧制的陶器表面复制,充分证明陶文为龙山时代的作品。就刻符排列而言,丁公陶文全篇有可认定的阅读方向,可以顺序而读,符合可以成句的条件。而冯时教授早已指出陶文曲线形体可以与古彝文联系。从考古信息、实体信息、刻符排列、刻符形体等各方面来看,丁公陶文已经符合作为远古文字的条件。
数千年前的远古文字还可以直接与现代文字作形体、意涵联系的文字,目前所知,除了汉字之外,只有彝文。笔者曾经利用音素归零法的数学模式间接推测境内汉字第二阶段发明期在公元前2100 年左右。丁公村遗址正在龙山时代晚期正是公元前2100年。所以汉字前身与丁公陶文可能都在此时进入由文至字的第二阶段文字发明期。以公元前2100年为关键时间点,未来文字考古一方面要从龙山晚期古国时代,上溯类似陵阳河刻符的“文”,一方面要从龙山晚期下探夏商之际王朝时代的“文字”。所以龙山丁公陶文在未来中国的文字考古占关键地位。
丁公陶文与古彝文的联系,表示境内除汉字系统外,至少还有彝文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新石器时代晚期。从面积、地理、人种、语言等种种因素来考虑,中国境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包括丁公陶文以及甲骨文前身的文字,相互竞争、影响。笔者曾经提出漏斗型模式来描述这种现象,认为汉字的前身就是经过“漏斗过滤”的选择形式而胜出,然后发展成为商代甲骨文形式的成熟汉字系统。
四种自源文字均为包括文与字的形音文字。其中以漏斗模式来描述的汉字从发明到发展至少有四千年,一脉相承连续。而拼音文字却在公元1000年完全与苏美、埃及等形音文字切断关系,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个现象可能可以联系到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以毕生考古研究心得比较东西文明,所提出的文明连续性与破裂性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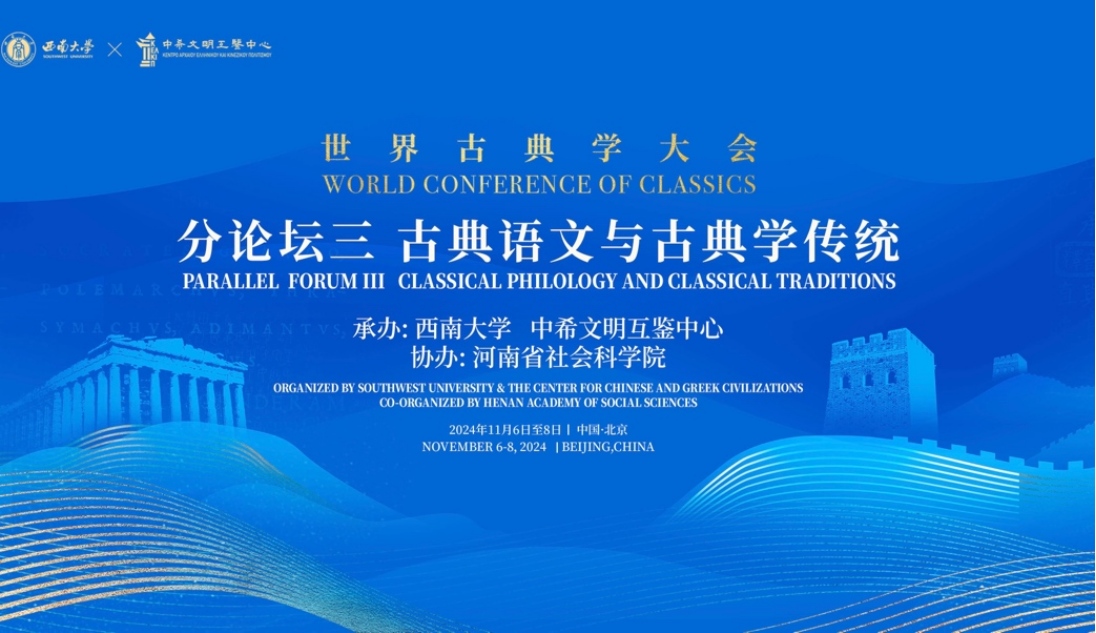
(本文系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主旨报告,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供稿、供图。)
















有话要说...